乌海日报
编辑:段继文
2024-12-26 09:2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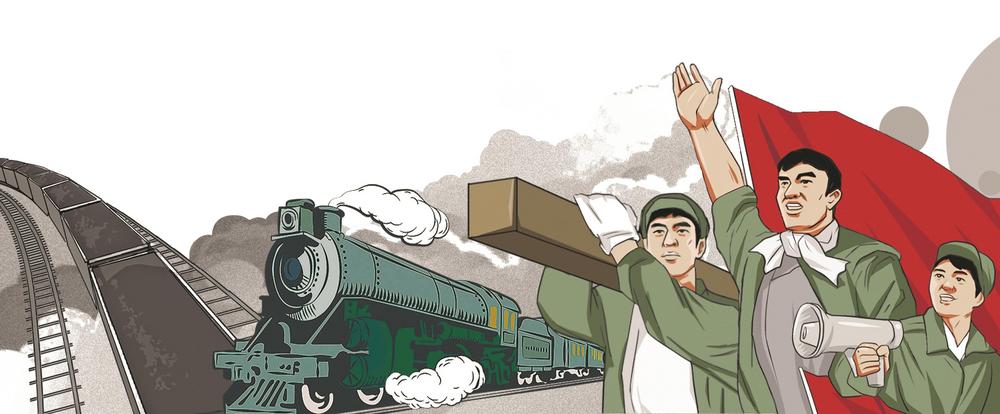
齐艳芳 绘图
本报记者 韩建慧
苍茫包兰线,如塞外长虹,穿大漠、跨黄河,绵延千里,连通三省,它唤醒了苍凉广袤的西北大地,让一座座煤都、铜城在大漠戈壁中拔地而起。
作为包兰线上重要的一站,乌海见证了这段被风沙磨砺的岁月,以至于六十多年之后再回顾,我们仍然要感叹,是父辈们大无畏精神创造了一部人定胜天的时代传奇。
这是一条贯穿三省,建在沙漠里的钢铁通途。
这条铁路,起自“草原钢城”包头,然后傍着黄河一路前行,穿越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平原,与腾格里沙漠擦肩而过,继而跨过连绵起伏的皋兰山区,将巴彦淖尔、乌海、石嘴山、银川、青铜峡、中卫等城市一一串联,最终到达兰州。
《内蒙古自治区志·铁路志》中是这样记载它的建设意义:“是沟通华北和西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也是北京通往西北的第二条通道,对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建设,促进沿线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沙漠之中铺铁路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沉睡千年的大西北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为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国家将修建包兰铁路列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铁道部开始对包兰铁路进行勘察设计。1957年3月,包兰铁路全面展开施工,以银川市为界,分东西两段,由包头市和兰州市分别向银川方向修建。
包头至银川的东段共长527公里,由铁道部华北设计分局(现更名为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北设计分局(现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勘察设计;1953年5月开始草测,1956年12月完成技术设计,1957年3月确定线路方向,过西山嘴(今乌拉特前旗附近)后大致沿黄河边行进,经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至磴口县三盛公后跨过黄河,再沿桌子山西麓至乌达区三道坎,再渡黄河到西岸后经石嘴山地区到银川。
这527公里也分为两个部分建设。其中从包头到乌拉特前旗公庙子段共90公里,由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现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修建,公庙子段至银川段的437公里则由铁道兵第一军和独立桥梁团负责修建。
于是,195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军率二、七、九师和独立桥梁团挥师北上,与铁道部工程局的工人们一起,开始了在沙漠中修铁路建桥梁的艰巨任务。
之所以说任务艰巨,那是因为这400多公里中,北部河渠纵横,桥涵和改渠工程多,有近130公里的地段,需要跨越大小渠流800余条;南部则要穿过150公里长的沙漠区,那里风沙弥漫,流动沙丘四伏,路基难筑;特别是还要修建三盛公和三道坎黄河大桥,这两座大桥是控制工期的关键工程。
按照设计规划,三盛公黄河大桥由12孔55米下承式钢桁梁组成,全长682.5米,桥梁基础施工采用蒸汽打桩机射水沉桩法,入土深度30至50米,全桥需要36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管桩408根;三道坎铁路大桥全长340.6米,由3孔55米下承钢桁梁和6孔28米钢板梁组成,桥墩为混凝土沉井基础。
工期吃紧,铁道兵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工地。但刚从包头换乘汽车前往磴口县三盛公,就遭遇到了特殊天气给的第一个“下马威”。曾是铁道兵战士的邓连贵就曾感慨地对本报记者说,由于往三盛公去的公路被黄沙所掩埋,大家只好边除沙开路边前行,300多公里的路程,硬是走了3天的时间。
这是1957年的早春。
桌子山下,四野不见绿色,户外滴水成冰。
罕有人烟的乌海地区,只有一些因开采小煤窑留下的破败房舍和部分放牧为生的“原住民”。当地人说,这里的天气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战士们对此深有体会。
邓连贵记得,由于当时没有住房,部队生活十分艰苦,人们靠着在工地上搭帐篷抵御夜晚的寒冷和风沙肆虐。除了帐篷,就只能挖地窨子或者盖“荆笆”房,那是一种用柳条和泥巴糊成的房屋,虽然四壁透风,但一间可以睡十来个人。
生活用水取自黄河,由部队安排汽车每天运输,遇上风沙最厉害的时候,汽车走不成,只好组织战士步行几公里去挑。有一次,派出挑水的战士遭遇沙尘暴,漫天风沙刮得睁不开眼,只好闭着眼睛摸索着往驻地走,等回了营房,一桶水只剩下了半桶。
尽管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但因为要赶工期,战士们还是头顶着黄沙、带着干粮和咸菜一头扎进包兰铁路的建设洪流中。
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修铁路,无论是铺设路基还是建设铁路桥皆需要克服一连串的技术问题。刚堆好的路基容易被风沙损毁,尤其是处在大风口的路基更是不稳。有别于现在的机械化施工,当时完全是重体力劳动。大筐挑土、抬土,一群人抡起石碾子夯土,昼夜施工,两班倒,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个小时。铁轨一节长12.5米,重达千斤。在当时连块砖运进来都难的条件下,铁道兵硬是靠着人力,一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一边靠着肩扛手推争工赶时,曾以日进10.455公里的速度,创造了当时全国人工铺轨的最高纪录。
沙海之中铸军魂
沙漠中铺铁轨不易,黄河上架桥同样艰难。
1957年春至1958年秋,是两座大桥的紧张施工阶段。铁道兵8502部队负责修建三道坎黄河大桥。这支英雄的部队,曾经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抢修过清川江大桥,也曾在祖国各地抢修和新建过许多座桥梁,但是在黄河上架桥,却还是第一次。
黄河的激流、冰冻以及春天的冰凌期,给建桥部队带来很多麻烦。当严寒到来的时候,黄河冰层有一米多厚,铁道兵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冰冻的黄河上施工。在沉井里作业的战士,就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每次从沉井里出来,头上都顶着一层冰霜。
为了防止黄河凌汛对桥体产生破坏,战士们冒着风寒,坚守在工地上游两岸,不断地爬冰堆,放炸药,奋战7昼夜,炸碎冰凌30多万立方米,化险为夷,保证了大桥的安全。
四号墩位于黄河的深水激流之中,墩身最长,又是全桥8个桥墩中开工最晚的一个,工程最为艰巨,铁道兵们把它比作三道坎黄河大桥上的“上甘岭”。
那时修铁路桥也没什么机械,仅有一台打桩机,还要靠十几个人拉重达150公斤的大砣来运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喊号子,打个十几分钟,就得换另一拨人。但就是这样,四号墩还是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提前完工。
三盛公和三道坎黄河大桥都高10多米,桥下就是滔滔的黄河水,由于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的安全系数小,人掉下去非死即伤。建桥过程中,有战士掉入浑浊的黄河水中,溺水而亡;也曾有操作蒸汽打桩机的战士,不慎坠入高温蒸汽锅炉中……
三盛公烈士陵园中曾有这样一幅碑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六一部队全体官兵、职工,奉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担负包兰铁路(包头—兰州)包银(包头—银川)段的修建任务。由于铁道兵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党、政、军的正确领导,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该部全体官兵、职工,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艰苦奋斗,干劲冲天,推动了全线工程的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提前五个月零六天建成。在执行这一艰巨光荣的任务中,有程志海等二十六名同志光荣牺牲,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使烈士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特建此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六一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立
注:刻碑文时牺牲26名,立碑后又牺牲3名,共29名。”
英雄浩气长存。
包兰铁路的建设历程,融入了广大参建铁道兵战士和沿途军民付出的大量心血。在修筑这段铁路和建桥施工中,共有29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龄最大者仅为34岁。他们被安葬在磴口县革命烈士陵园,后迁往呼和浩特大青山革命烈士公墓(今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人祭奠。
战士卸甲气如虹
1958年7月,包兰铁路建成,达到了通车条件,比原计划提前五个月零六天。8月1日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是年末,堪称乌海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也在汽笛长鸣声中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包兰铁路通车后,由于当时铁路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投入维护,在祖国的一声召唤下,成千上万的铁道兵脱下军装,纷纷转业到包兰铁路沿线地区,成为光荣的铁路工人,继续为铁路建设和地区发展作贡献。
由于深受风沙危害,刚开通运营时,包兰线平均每年发生沙害断道300余次,火车被迫停开等情况时有发生,曾有国外专家预言:包兰铁路“存活”不了30年就会被沙漠淹没。但铁路人不信,他们扎根沙漠,一锹一锹,把包兰线从漫漫黄沙中铲了出来。
为了对抗沙漠的侵袭,经过反复试验,铁路人摸索出“麦草方格沙障”,并在草方格上栽种沙蒿、花棒、籽蒿、柠条等沙生植物;建起了4级扬水站,将流经沙坡头的黄河水引到沙丘上,提高了林木成活率;夷平了上千座沙丘,开垦出2000多公顷沙地,在铁路边建起了一座座沙漠果园……
时间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宁夏沙坡头,绿意盎然,以包兰铁路为中心,大片绿洲向外延伸开来,而沙坡头的治沙经验,也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被赞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荒漠逐渐变成了绿洲,包兰铁路为沙漠辟出绿色长廊。
而对于乌海人民来说,包兰铁路的通车,除了给乌海地区的煤炭资源外运提供了先决条件外,老百姓也终于在家门口坐上了火车。
时光川流不息。
时至今日,倘若你要问,包兰铁路的建设,对于包括乌海在内的西部诸多城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时间会告诉你,作为中国的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的修建在中国的治沙史和铁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乌海日报社 | 2024-12-26 09:29:02
乌海日报社 | 2023-10-16 09:03:12
乌海日报社 | 2023-10-16 09:02:37
乌海日报社 | 2023-10-16 09:01:36